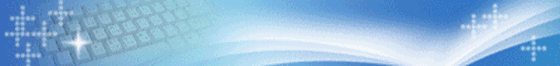熱河
E
澳門街,彈丸之地,人口稠密,石屎森林建得有聲有色。在舊區,“林中小路”大多只容得下單線行車,橫街窄巷多不勝數,建築物之間,經常只有十米不到的距離。樓高五、六層的唐樓,比比皆是,綠的灰的,每家每戶端出款式各異的透明壓花玻璃窗,花樣講究的露台圍欄,像穿旗袍、年屆耄耋的老女人,幾分源自上世紀的風韻猶存。
三十歲文藝男青年陳明宇,和妻子一起住進舊城區某唐樓的四樓單位,樓齡五十年,附一副長方形露台。這是祖父母過世後遺留下來的空置單位,兩夫妻新婚後仍在存錢買洋房,目前只好先暫住於此。樓下的單位住了陳明宇的父母,婚前陳明宇也住在那裡,婚後把日用品搬到樓上,再沿用祖父母的舊家具,打算湊合着住上一年半載。陳明宇很喜歡這單位的露台,能放一張藤椅,躺着吹吹風。小時候他常跑到樓上玩耍,躺在藤椅上看書,或偷玩GameBoy。現在,人大了,站在這充滿回憶的露台上,曬曬太陽,種幾盆花草,彈結他,吸收一點懸浮在城市上空的新鮮廢氣,已是像他這樣肚腩微凸、不時被左鄰右里幾個小屁孩喚作“叔叔”的平凡小卒們的人生樂事。
夫妻二人在同一間娛樂場工作,需輪班,幸運時一齊上下班,陳明宇會開着他的二手豐田,載妻子一同出門或回家。但大多時候,兩人的排班交錯,即便如此,出於責任,若然陳明宇有空,也會盡量開車去氹仔接送妻子,畢竟小城人多車多,擠巴士辛苦又費時,攔的士又貴又受氣。
雖然結婚才幾個月,但拍拖五年,愛情的熾熱之火已消磨不少,陳明宇每日最期盼的,反而是獨處的靜謐悠閒。
一天清晨,兩人下班,陳明宇如常載妻子回家。又如常,妻子二話不說走入睡房,埋頭大睡。陳明宇抱起他的古典結他,推開微微生銹的露台鐵門,踏入他們家的“後花園”。一個回身,將鐵門關嚴,然後仰躺在舒爽的藤椅上。這個“後花園”,像一隻長方形小船,被幾盆薄荷和富貴竹包圍。他長舒一口氣,長夜漫漫過後,終於將疲憊的一天,褪在陰沉的俗世之海中。
陳明宇彈奏起他最愛的中國現代民謠,幻想自己沐浴於不羈的青春浪漫狂潮之中。
其中,他最近愛上並反覆練習的,就是李志的《熱河》。
熱河路有一家開了好多年的理髮店
不管剪甚麼樣的髮型你只要付五塊錢
老板和他的妹妹坐在椅子上對着鏡子一言不發
他們的老家在身後在岸邊在安徽全椒縣
他想像自己走在熱河路上,他沒去過那地方,不知道在安徽還是南京,甚至不肯定南京是不是在安徽省。那地方應該很熱,有一條混濁的河,有一家老舊的理髮店,很傳統,像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還會為客人們提供熱氣騰騰的白色早安巾的那種店;或者像兒時很怕,但父親總是令人費解地堅持帶他去,門外會賣六合彩的,澳門老式理髮店。
紀念碑旁有一家破舊的電影院
往北走五百米就是南京火車西站
每天都有外地人在直線和曲線之間迷路
氣喘吁吁眼淚模糊奔跑跌倒奔跑
他幾乎哭了出來。他想起從未去過的南京,再想到遊盪在後海酒吧的夏夜。在澳門,他是本地人,卻像外地人,因為他也在直線和曲線之間迷路,在七彩霓虹的魅影中,在奇特魔幻的中西建築群中,在現代和古代的板塊裂縫中,在一刻不停地盤根栽植的石屎叢林中,他喘着氣,不知去向地奔跑、迷失、再奔跑、再迷失。
僅咫尺之距,忽然,有一把歌聲,順着他指間的六弦遊走,像走鋼索。這一把歌聲,很擅長走鋼索,平衡感一流,走得很穩。陳明宇既驚又喜。他不想打擾這把完美的歌聲,像不願嚇跑電線桿上的麻雀。他記得電視上的歌唱節目,評審起初也背對着參賽選手,保持神秘感。他冷靜下來,和歌聲的主人,合作彈唱完這首《熱河》。
這把歌聲,極之優雅而自信地在鋼索上漸漸停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陳明宇霍地站起,舉目越過一盆薄荷葉。一幢灰綠色的唐樓上,同樣是四樓,和他相對的露台,一位約莫三十來歲的男子,身材頗壯健,架起粗框眼鏡,小平頭,長得成熟而俊朗,卻又透出幾分萎靡。男子穿着一件白淨無袖汗衫,坐在摺凳上。他微微一笑,眼神綻放出光芒。
男子沙啞的聲線沉進熱河,清晨溫和的日光灑落於一片盆綠上。他站起來,舉起手邊的啤酒,向陳明宇致意。陳明宇連忙跑進廚房,打開雪櫃,拿出一罐冰凍的青島。兩人隔着一條狹窄街道,在各自的“後花園”上,掏出江湖豪傑義薄雲天的氣派,吞下一整座青島。
A
此後數天,陳明宇精神抖擻,內心住進了一匹奔騰的野馬。和往常一樣,沉默地開車前往娛樂場,沉默地工作。下班後,他急不及待趕回家,一頭躍進陽光明媚的熱河。有人說,把兩個人活成一個人,是理想的愛情生活;對陳明宇來說,這個浪漫句子的含意卻恰恰相反,他幾乎把妻子忘得一乾二淨!
每當他把自己鎖進狹小的露台,抱着寶貝結他,從手指在金屬弦線上撥弄出第一個和弦開始,他彷彿唸起召喚天籟之聲的咒語。前奏過後,將雲霧劃開的那一句“熱河路就像八十年代的金壇縣”,總會準時報到。男子低沉的沙啞嗓音,像咕碌咕碌灌下肚的冰凍啤酒,滑過陳明宇的喉嚨,直達心臟,如電流通過,觸電似地震顫。
他從未經歷過這種,甚至比冰涼啤酒更直透心底的震顫,以及隨之而來,充盈全身的熱血。他彈得不那麼工整了,多了一分隨性寫意,有時,更可謂全然的即興和狂野。
清晨過後,他不得不酒酣耳熱地回到睡房,回到妻子身旁。但他不禁想像男子的生活:他也回去睡覺嗎?還是準備外出工作?他整天都會練唱嗎?沒想到在澳門,竟然有人和他一樣,喜歡中國民謠,還唱得如此銷魂。一想到這,陳明宇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陳明宇常常信步走出露台,以茂密的盆栽作掩護,探頭探腦,往對面的露台望去。目光穿過那神秘的露台,多數時候,那個單位卻一片昏暗。露台的鐵門牢牢地關起來,窗戶也緊閉,壓花玻璃只能透光,除了電視機畫面偶爾的閃爍,他甚麼都看不見。如果說那是一個空置單位,不明就裡的人也會相信。
不過,每窺看十次,總有一兩次,陳明宇是看得見男子的。他會穿着白色或灰色,無袖或有袖的汗衫,坐在摺凳上讀報紙,或晾掛衣服。有一次,他和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太太一起,在露台上吹風,兩人沉默不語。這位老太太不過六七十歲年紀,一頭銀髮整齊地往後梳,看起來應該是他母親。
後來,每次看見獨自一人呆在露台上的男子,陳明宇都會彈一首歌,大多是李志的歌,《梵高先生》、《山陰路的夏天》、《關於鄭州的記憶》、《和你在一起》、《天空之城》等等。男子順着陳明宇彈奏的結他,展露他低沉、沙啞而性感的歌喉,把當時的心情,全神貫注在歌曲中。
某天,陳明宇上完早班,妻子的晚班才剛開始。傍晚回到家,喝兩罐啤酒,微醉之下,他埋入藤椅的懷抱,彈起趙雷的《成都》。他暗自期盼着,熟悉的低沉嗓音會加入這趟成都之旅中。但沒有,也許男子沒有那個興致。
也許,他不會唱《成都》?此刻他才回想起,男子也只有在他彈李志的歌時,才會跟着音樂唱起來。陳明宇像機械人一樣撥弄弦線,卻已神遊太虛。
他不其然滑進夢鄉。燈紅酒綠的成都,他竄進寬窄巷子,身後牽了一隻手。那隻手十分溫暖,極粗糙,決不是他妻子的手。
他回頭一看,夢醒了。這個夢,把他嚇出一身冷汗。
D
陳明宇睜開眼,一隻紙飛機在一盆富貴竹上墜毀,一頭插進竹葉之間。他好奇地打量這架典型的尖嘴機。和其他小孩一樣,小學時期的陳明宇,也曾醉心研發不同型態的紙飛機,最後發現還是這簡單又好看的款式,飛得最遠最穩定。
他拆開飛機,發現那是一張A4大小、從電腦列印出來的《熱河》C調結他譜,上面還有歌詞。曲譜最下面,用原子筆寫上了一個WeChat ID。那個男人似乎是看見了在藤椅上睡覺的陳明宇,便摺了一架紙飛機,想告訴他自己的聯絡方式。此刻,那房子看似沒有人,客廳裡只隱約散發出神枱燈微弱的紅光。
陳明宇煮了一碗公仔麵,吃飽後回睡房準備睡覺。躺在床上,他打開WeChat,加了那個ID。男人的ID名字是“一顆栗子”。他不明白,堂堂一個成熟俊朗、鬍渣滿臉的男人,怎麼會用這種可愛的名字?好奇心牽引下,他打開“一顆栗子”的朋友圈,一直往下滑。
他的朋友圈,大部分由一些澳門和內地的風景照所組成。從照片可見,他是李志的忠實粉絲,去過他在台灣和北京的演唱會。他不自拍,但有時會在家裡或公園幫母親拍照,她偶爾會笑一笑,多數時候很木訥。
有一張她母親坐在輪椅上,戴着老花眼鏡專注讀報的照片,“一顆栗子”配上這樣一段文字:媽媽,我是多麼愛你,當你沉默的時候我愛你。那是《這個世界會好嗎》的歌詞,他想必唱過上千次了。另外,某張兩人在公園的合照上,他配上了這樣的文字:老媽子說我唱的《熱河》不知所云,像和尚誦經呢喃!
雖然一星期才更新一兩次,貼文不算多,但陳明宇在栗子的朋友圈裡逛了整整半小時。不時按了一些“讚”,特別是在和李志或音樂有關的話題上。
其中有兩條動態令陳明宇印象深刻:第一條是在兩年前,他貼了一張熊熊烈火正在燃燒的照片,非常吸引眼球。烈焰中,一堆曲譜隱約可見,他是在仿效多年前放火燒燬自己唱片的李志嗎?他付之一炬的,是李志的曲譜嗎?還是他自己寫的歌?由於照片中的曲譜大部分已燒成灰燼,只能勉強辨認出六線譜和少數幾個和弦,曲譜上的內容,就成了一個謎。
圖片附上文字:我們生來就是孤獨。
另一條耐人尋味的貼文,發佈於去年。照片的背景應該在家裡,照片中一把被砸破的結他靠在一個牆角上。一縷陽光灑進,使這隻死亡的結他更顯孤寂與淒美。這則貼文也附上文字:
再見,音樂!
簡單而悲傷的宣言,“一顆栗子”似乎是一個曾放棄音樂的人,昔日的音樂狂熱愛好者。
陳明宇回想起來,這段時間一直彈李志的歌,也算是對他的撫慰吧。在澳門,突然遇上像他這樣的知音,栗子哥的內心想必也是無比激動的吧。
陳明宇睡了一覺,醒來時發現栗子給他傳了一則問候訊息。從此,他們常常用WeChat聊天,聊音樂、聊社會、聊人生。陳明宇問他為甚麼叫“一顆栗子”,他說李志的名字,用普通話唸,和荔枝和栗子都差不多,但荔枝太女性化,栗子比較適合。陳明宇覺得,栗子也不見得有多男性化。
“既然你也喜歡李志,要不你叫‘荔枝’吧。”
陳明宇無所謂,反正只有“一顆栗子”會用這暱稱。
他們還約定了,以後有機會要一起去南京看李志的演唱會,一起走在安徽的熱河路上。
G
某個傍晚,陳明宇載着妻子和父母,一同前往某酒店參加家族聚會。出於好奇,開車出發時,陳明宇瞥了一眼“一顆栗子”的大廈門口。他竟然馬上看見了那個男人。
“一顆栗子”彎起腰,從輪椅上揹起老太太。他步履蹣跚,打開樓梯間暗沉的鎢絲燈,喘起粗氣,拾級而上。那張輪椅就靜靜地待在大廈門口,像等待被接走的小孩。
陳明宇很想過去幫他,至少幫他把輪椅抬上去,免得他要多走一趟。妻子瞪了他一眼,說他們要遲到了,讓他別多管閒事。
他們是大家族的一分子,每次聚會都有三四十位親戚出席,你一言我一語,唾沫橫飛,說三道四,他和妻子都十分厭倦。但這種定期聚會,對兩夫妻而言,是責任,彷彿是婚姻生活中不可抹去的一環,他們也只好乖乖赴會。和往常一樣,親戚們對他倆評頭品足,從身材評到家財,再到他們暫住的家的每件家具,每個細節都不肯放過,彷彿二人的生活就是他們茶餘飯後賴以維生的娛樂。
這些陳明宇都忍下來了,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他們總喜歡談論文化、文學、音樂,以顯示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品味。對世界上任何藝術而言,外行人永遠是談論得最熱烈的。這個晚上,他們把民謠和搖滾批評得一文不值,說這些亂七八糟的音樂都是過去所謂的靡靡之音,不過是吸毒者的海洛英,無病呻吟者的興奮劑;同時,他們歌頌流行音樂中非關愛情的歌曲是何等偉大,且琅琅上口。陳明宇實在聽不下去,跑到酒店外吹風、抽煙。
他發現“一顆栗子”傳了一則訊息給他。
“在幹甚麼?”後面加了一個“親嘴”的表情符號。
這個圖案有點不同尋常,陳明宇當下不敢回應。
隔了一會,陳明宇又收到栗子的一則訊息:“一個人嗎?”
隔了兩天,陳明宇才回覆他,但假裝沒見過那兩則訊息。而“一顆栗子”也沒說甚麼,他沒有再用過表情符號。
不久,陳明宇知道“一顆栗子”是的士司機,從早上開車開到黃昏。每個禮拜,他都會抽一個下午,花兩小時,開着他租回來的的士,回家載母親去兜風,陪她去盧九花園走一走。
幾天後,又是一起下班的清晨,陳明宇趁妻子回睡房休息,又興致勃勃地回到他的“後花園”。不過,那是一個下着滂沱大雨的清晨,豆大的雨點“咚咚咚”地敲在各家各戶的屋簷上。
在陰沉鬱悶的天氣下,陳明宇彈了一首《這個世界會好嗎》。
彈了兩遍,對面露台仍寂靜無聲。陳明宇有點失望。
此時,“一顆栗子”來電。
“我聽不清楚你彈的結他,能開着手機讓我聽嗎?”雨聲很大,但栗子說得很沉穩,稍稍放大了他低沉的嗓音。
雖然認識了一段時間,但這是栗子第一次直接和陳明宇對話。
於是兩人就以手機作為“喇叭”,合作演繹這首《這個世界會好嗎》。
媽媽,我是多麼愛你
當你沉默的時候我愛你
陳明宇聽他唱出這段,腦海裡浮現的,是他母親的照片,以及那個黃昏,高大的他,佝僂着背,揹着瘦小的母親回家。
這首歌,栗子唱得特別有感情,一貫高水準而帶有磁性的歌聲,挾帶了些許哭腔。
媽媽,我居然愛上了他。
像歌唱一樣就愛上了他。
聽着電話另一頭栗子清晰地唱出每一個字句,陳明宇忽然很難過。這首歌就像是一個痛苦的人,對世界的詰問。
而他也只有那一個既愛且恨的“媽媽”了。
一曲唱畢,兩人無言。
十秒過去。
二十秒過去。
三十秒過去。
兩人不知不覺地屏住了呼吸,沉默只能以滴滴答答的雨水填塞,早已超越了使氣氛變得尷尬的臨界線。兩人沒有任何客套的讚美或問候,又不願掛線,似乎都在等待着甚麼。
終於,手機那一頭的人說話了。
“荔枝……人,為甚麼會寂寞?”
陳明宇背對着栗子,他無法想像,十米以外的那一個人,正以怎樣的眼神凝望着他。
突然,一聲巨響從電話那頭傳來。栗子跑進屋內,一陣慌亂。
B
後來,栗子向陳明宇解釋,他家客廳有一塊石屎毫無預警地塌了下來,把他和母親嚇呆了。雖然只有一巷之隔,栗子的大廈比陳明宇的還要老上十年。陳明宇很好奇栗子和老太太為甚麼不搬家,搬到有電梯的房子,小一點沒關係,最重要是方便。而且石屎都掉下來了,萬一砸在人的頭上,後果真不堪設想。相比起快要搬走的他,栗子無疑是更需要搬去電梯洋房的人。
陳明宇告訴栗子,一個月後,他們就要搬去氹仔。栗子看起來很為他高興,和他相約在露台上喝酒。
那天,他們從傍晚一直喝到凌晨,一邊彈唱李志的歌,一邊喝酒,甚麼都沒說,只是一首接一首地唱,簡直成了一個山寨版的李志音樂會,幾乎把每一首李志的歌都唱了一遍。鄰居們走出露台投訴了好幾次,他們卻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陳明宇的妻子罵也罵過了,拉也拉過了,還差點被醉醺醺的陳明宇用一個盆栽砸破頭。直到夜深人靜,大家都沒力氣埋怨了,他們自己也彈累了唱累了,就倒在各自的露台上,打起呼嚕,睡得不省人事。
中午,陽光把陳明宇曬醒。他望一望對面,栗子不在了。他這才慢慢想起,那個男人,雖然昨夜甚麼都不說,卻一定是藉着李志的歌,把要說的都說完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陳明宇沒怎麼見過栗子,彈結他他也沒回應。偶爾,陳明宇從對面露台上找不着他,就會往下望,然後看見他揹着老太太坐上的士,或從的士上把她扶上輪椅。他總是一個人忙進忙出,照顧老太太。但他不唱歌了,也許這段時間他太累了,沒力氣唱歌。
也許栗子已經把前陣子的山寨音樂會,當成對他的告別。
陳明宇搬走前幾天,正在收拾一些準備搬到新家的日用品。某個清晨,他從睡房中隱約聽見一把熟悉的歌聲。那聲音一下子直抵他心靈深處,他不可能認不出來。他馬上跑到露台。推開生銹的鐵門後,映入眼簾的一幕,他這輩子都忘不了。
對面露台上,栗子坐在平時的摺凳上,為背對着他、坐在輪椅上的老太太剪頭髮。陽光溫和地灑落在兩人身上。老太太的頭髮依舊整齊,只是剪得更短了,陽光在她銀白的髮絲上,閃爍着耀眼的光芒。一根根頭髮落在鋪滿報紙的地板上。
栗子唱着他們三人都很熟悉的那首,《熱河》。老太太很安靜,感覺不出她對這首歌的厭煩。不過,這一次,栗子的歌聲不像往常般沉穩自信,而是搖搖欲墜。一顆淚珠從水汪汪的雙眸中滾了下來。
如果年輕時你沒來過熱河路
那你現在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
陳明宇拿起結他,跟上栗子的節奏,手指顫巍巍,彈起了同樣搖搖欲墜的《熱河》。
他們最後一次共同完成一首歌,就在這麼一個明亮而傷感的早上。
隔天早上,陳明宇聽見救護車的鳴笛聲,隱然有股不祥之感。他跑出露台,只見救護車停在對面大廈門口。過了一會,醫護人員抬着擔架把栗子的母親抬出來,栗子和她一起,上了救護車。救護車匆忙地向醫院馳去。
那是陳明宇最後一次看見栗子。幾天後,陳明宇和妻子搬走了。此後,陳明宇嘗試用微信跟栗子聯絡,但他已不再回應,朋友圈也不再更新。
E
三年後,為了見識那條骯髒又親切的熱河路,陳明宇一個人去了南京。
當他坐在一家老式理髮店中,給師傅修剪一個五塊錢埋不了單的髮型時,他正在吃栗子。也就在這時,撇除了三年來無數次無意識的想念,他有意識地想起了“一顆栗子”。
他想像那個男人吃荔枝的樣子。腦海中迴盪起他的歌聲,陳明宇依舊感到溫暖。
想到他的無知,陳明宇不禁莞爾。他很想告訴栗子,熱河路是在南京,不在安徽省。
然後,他高聲唱起那首他們都熟悉的歌。
沒有新的衣服能讓你愛戀
總有一種天氣讓我懷念
醒來或者吃飽又是一年
相遇然後分別就在一天
古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