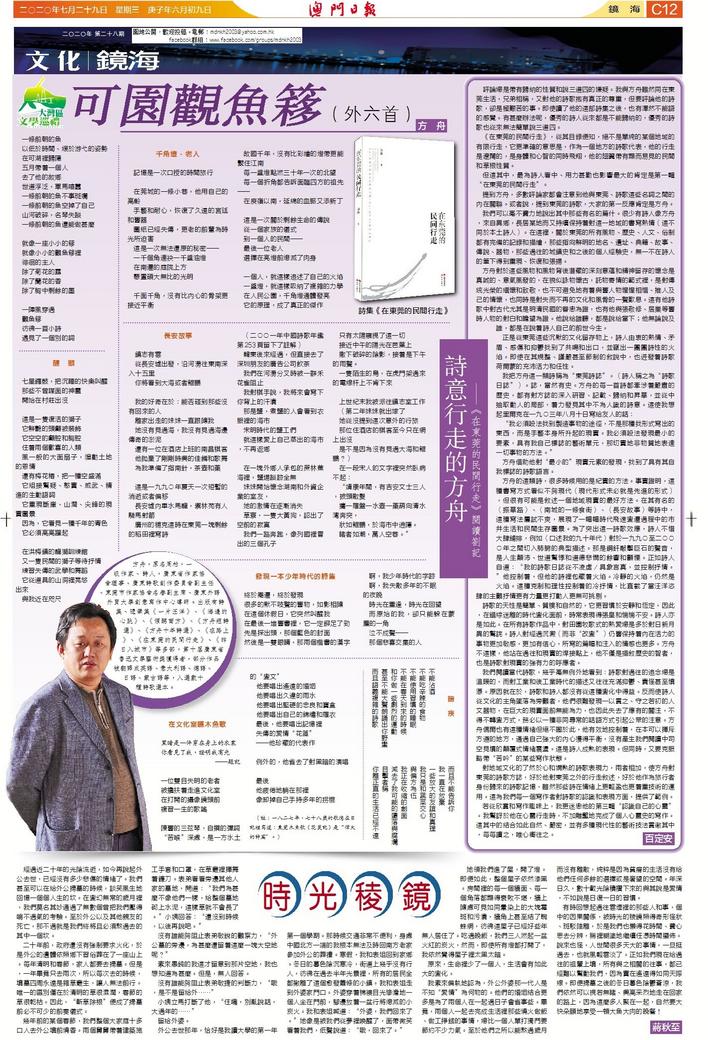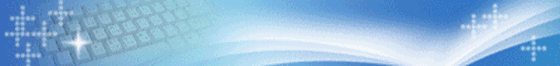可園觀魚簃(外六首)
一條前朝的魚
以低於時間、緩於游弋的姿勢
在可湖裡歸隱
五月帶着一個人
去了他的故鄉
世道浮泛,軍馬喧囂
一條前朝的魚不事斑斕
一條前朝的魚空掉了自己
山河破碎,名琴失蹤
一條前朝的魚還能做甚麼
就像一座小小的簃
就像小小的觀魚簃裡
徘徊的主人
除了菊花的露
除了蘭花的香
除了胸中剩餘的墨
一陣風穿過
觀魚簃
彷彿一首小詩
遇見了一個別的詞
醒 獅
七星鑼鼓,把沉睡的快樂叫醒
那些不曾謀面的神靈
開始在村莊出沒
這是一隻復活的獅子
它鮮艷的頭顱被裝飾
它空空的顱腔和胸腔
住着兩個歡喜的人類
風一般的大面扇子,煽動土地的恩情
還有梅花樁,把一種空盛滿
它組接驚疑、憨實、威武、精進的生動語詞
它重現斷崖、山澗、尖鋒的現實圖景
因為,它看見一種千年的青色
它必須高高躍起
在洪梅鎮的龍獅訓練館
又一隻民間的獅子等待抒情
練習失傳的武學和舞蹈
它從道具的山洞裡晃悠
出來
與我近在咫尺
千角燈 · 老人
記憶是一次口授的時間旅行
在莞城的一條小巷,他用自己的高齡
手藝和耐心,恢復了久遠的宮廷和舊器
圖紙已經失傳,更老的前輩為時光所迫害
這是一次無法還原的秘密——
一千個角連袂一千盞油燈
在南遷的庭院上方
懸置碩大無比的光明
千面千角,沒有比內心的骨架更接近平衡
故國千年,沒有比彩繪的燈帶更能繫住江南
每一盞燈點燃三十年一次的北望
每一個折角都告訴面臨四方的祖先——
在庾嶺以南,延綿的血脈又添新丁
這是一次關於剩餘生命的傳說
從一個家族的儀式
到一個人的民間——
最後一位老人
選擇在亮燈前熄滅了肉身
一個人,就這樣追述了自己的火焰
一盞燈,就這樣吸納了複雜的力學
在人民公園,千角燈通體發亮
它的原理,成了真正的傑作
長安故事
鎮志有雲
從長安墟出發,沿河湧往東南深入十五里
你將看到大海或者鯤鵬
我的好奇在於:能否碰到那些沒有回來的人
離家出走的妹妹一直跟隨我
她沒有見過海,我沒有見過海邊傳奇的淤泥
還有一位在酒店上班的南昌棋客
他拋棄了剛剛時興的佳餚和歌舞
為我準備了指南針,茶壺和藥
這是一九九○年夏天一次短暫的消逝或者偏移
長安墟內車水馬龍,禦林苑有人騎馬射箭
廣州的楊克這時在東莞一塊剩餘的稻田裡寫詩
(二○○一年中國詩歌年鑑第253頁留下了註解)
韓東後來經過,但直接去了深圳朋友的廣告公司飲茶
我們在河湧分叉時被一群禾花雀阻止
我對棋手說,我將來會寫下你背上的汗漬
那是鹽,煮鹽的人會看到衣服裡的海市
宋明時代的鹽工們
就這樣愛上自己蒸出的海市,不再返鄉
在一塊外鄉人承包的蔗林蕉海裡,鹽場蹤跡全無
妹妹開始懷念湖南和外資企業的室友,
她的激情在逐漸消失
草寮,一隻大黃狗,認出了空前的寂寞
我們一路奔跑,像列國裡冒出的三個孔子
只有太陽窺視了這一切
接近中午的陽光在芭葉上
撒下破碎的陰影,接着是下午的雨聲。
一隻陌生的鳥,在虎門架過來的電線杆上不肯下來
上世紀末我被派往鎮志室工作
(第二年妹妹就出嫁了
她從沒提到這次意外的行旅
那位住酒店的棋客至今只在網上出沒
是不是因為沒有見過大海和鯤鵬?)
在一段宋人的文字裡突然臥病不起:
“靖康年間,有吉安文士三人,披頭散髮
攜一羅盤一水壺一藥葫向清水灣奔突,
狀如鯤鵬,於海市中逍隱。
睹者如潮,萬人空巷。”
發現一本少年時代的詩集
終於喬遷,終於發現
很多的默不吱聲的舊物,如影相隨
在這個休假日,它突然叫醒我
在最後一堆舊書裡,它一定鉚足了勁
先是探出頭,那個藍色的封面
然後是一雙眼睛,那兩個楷書的漢字
啊,我少年時代的字跡
啊,我失散多年的不眠的夜晚
時光在重逢,時光在回望
而原始的我,卻只能躲在蒙塵的一角
泣不成聲——
那個悲喜交集的人
在文化室聽木魚歌
黑暗是一件穿在身上的衣裳
你看見了我,證明我有光
——題記
一位雙目失明的老者
被攙扶着走進文化室
在打開的攝像鏡頭前
複習一生的歌謠
陳舊的三弦琴,自撰的彈詞
“苦喉”深處,是一方水土的“變文”
他要唱出遙遠的婚姻
他要唱出久違的雨水
他要唱出堅硬的忠良和寶盒
他要唱出自己的錦繡和羅衣
最後,他要唱出記憶裡
失傳的愛情“花箋”
——他珍藏的代表作
例外的,他省去了對黑暗的演唱
最後
他疲倦地躺在那裡
像卸掉自己手持多年的拐棍
(註:一八二七年,七十八歲的歌德在日記裡寫道:東莞木魚歌《花箋記》是“偉大的詩篇”。)
暗 疾
不能沾酒
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不能使用習慣的睡眠
不能在春天到來的時候
和你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甚至不能大聲朗誦出你野蠻
而且語義複雜的詩歌
而且不能告訴你
我一直在放棄
一些放大的友誼和真理
我只是和蔬菜交心
與偏方為伍
我正在收縮的創面
減去了我可能的墮落與腐爛
目擊者稱
你離正直的生活已經不遠
方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