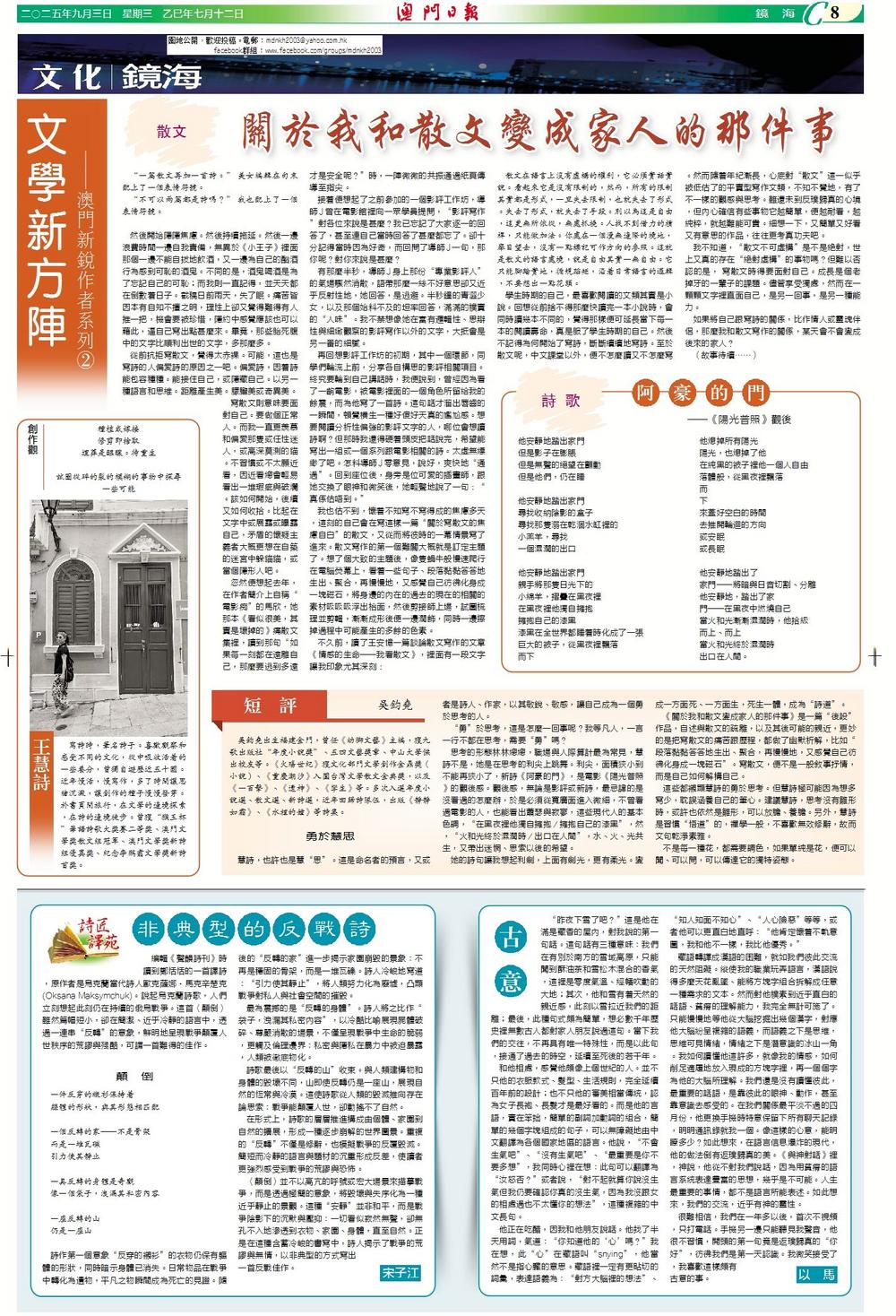散文
關於我和散文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一篇散文再加一首詩。” 美女編輯在句末配上了一個表情符號。
“不可以兩篇都是詩嗎?” 我也配上了一個表情符號。
然後開始隱隱焦慮。然後持續拖延。然後一邊浪費時間一邊自我責備,無異於《小王子》裡面那個一邊不能自拔地飲酒,又一邊為自己的酗酒行為感到可恥的酒鬼。不同的是,酒鬼喝酒是為了忘記自己的可恥;而我則一直記得,並天天都在倒數着日子。截稿日前兩天,失了眠。痛苦皆因本有自知不擅之明,理性上卻又覺得難得有人推一把,機會要被珍惜,隱約中感覺應該也可以藉此,逼自己寫出點甚麼來。畢竟,那些胎死腹中的文字比順利出世的文字,多那麼多。
從前抗拒寫散文,覺得太赤裸。可能,這也是寫詩的人偏愛詩的原因之一吧。偏愛詩,因着詩能包容種種。能接住自己,或隱藏自己。以另一種語言和思維。距離產生美。朦朧美或奇異美。
寫散文則意味要面對自己。要做個正常人。而我一直更羨慕和偏愛那隻或任性迷人,或高深莫測的貓。不習慣或不太願近看,因近看總會輕易看出一堆瑕疵與破爛。該如何開始,後續又如何收拾。比起在文字中或展露或曝露自己,矛盾的懷疑主義者大概更想在自築的迷宮中躲貓貓,或當個隱形人吧。
忽然便想起去年,在作者簡介上自稱“
電影痴”的馬欣,她那本《看似很美,其實是壞掉的》痛散文集裡,讀到那句“如果每一刻都在遠離自己,那麼要逃到多遠才是安全呢?”時,一陣微微的共振通過紙頁傳導至指尖。
接着便想起了之前參加的一個影評工作坊,導師J曾在電影館裡向一眾學員提問,“影評寫作”對各位來說是甚麼?我已忘記了大家逐一的回答了,甚至連自己當時回答了甚麼都忘了。卻十分記得當時因為好奇,而回問了導師J一句,那你呢?對你來說是甚麼?
有那麼半秒,導師J身上那份“專業影評人”的氣場驟然消散,語帶那麼一絲不好意思卻又近乎反射性地,她回答,是逃避。半秒鐘的青澀少女,以及那個始料不及的坦率回答,滿滿的樸實的“人味”。我不禁想像她在富有邏輯性、思辯性與細緻觀察的影評寫作以外的文字,大抵會是另一番的細膩。
再回想影評工作坊的初期,其中一個環節,同學們輪流上前,分享各自構思的影評相關項目。終究要輪到自己講話時,我便說到,曾經因為看了一齣電影,被電影裡面的一個角色所留給我的餘震,而為他寫了一首詩。這句話才溜出唇齒的一瞬間,頓覺横生一種好傻好天真的尷尬感。想要閱讀分析性偏強的影評文字的人,哪位會想讀詩啊?但那時我還得硬着頭皮把話說完,希望能寫出一組或一個系列跟電影相關的詩。太虛無縹緲了吧。怎料導師J零意見,說好,爽快地“通過”。回到座位後,身旁是位可愛的插畫師,跟她交換了眼神和微笑後,她輕聲地說了一句︰“
真係估唔到。”
我也估不到,懷着不知寫不寫得成的焦慮多天,這刻的自己會在寫這樣一篇“關於寫散文的焦慮自白”的散文,又從而將彼時的一幕情景寫了進來。散文寫作的第一個難關大概就是訂定主題了。想了個大致的主題後,像隻蝸牛般慢速爬行在電腦熒幕上,看着一些句子、段落黏黏答答地生出、聚合,再慢慢地,又感覺自己彷彿化身成一塊磁石,將身邊的內在的過去的現在的相關的素材吸吸吸浮出枱面,然後剪接師上場,試圖梳理並剪輯,漸漸成形後便一邊潤飾,同時一邊擦掉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多餘的色素。
不久前,讀了王安憶一篇談論散文寫作的文章《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裡面有一段文字讓我印象尤其深刻︰
散文在語言上沒有虛構的權利,它必須實話實說。看起來它是沒有限制的,然而,所有的限制其實都是形式,一旦失去限制,也就失去了形式。失去了形式,就失去了手段。別以為這是自由,這更無所依從,無處抓撓。人找不到借力的槓桿,只能做加法。你處在一個漫無邊際的境地,舉目望去,沒有一點標記可作方向的參照。這就是散文的語言處境,說是自由其實一無自由。它只能腳踏實地,循規蹈矩,沿着日常語言的邏輯,不要想出一點花頭。
學生時期的自己,最喜歡閱讀的文類其實是小說。回想從前捨不得那麼快讀完一本小說時,會同時讀幾本不同的,覺得那樣便可延長當下每一本的閱讀壽命,真是服了學生時期的自己。然後不記得為何開始了寫詩,斷斷續續地寫詩。至於散文呢,中文課堂以外,便不怎麼讀又不怎麼寫。然而隨着年紀漸長,心底對“散文”這一似乎被低估了的平實型寫作文類,不知不覺地,有了不一樣的觀感與思考。雖還未到反璞歸真的心境,但內心確信有些事物它越簡單,便越耐看,越純粹,就越難能可貴。細想一下,又簡單又好看又有意思的作品,往往更考真功夫吧。
我不知道,“散文不可虛構”是不是絶對,世上又真的存在“絶對虛構”的事物嗎?但難以否認的是, 寫散文時得要面對自己。成長是個老掉牙的一輩子的課題。儘管享受獨處,然而在一顆顆文字裡直面自己,是另一回事,是另一種能力。
如果將自己跟寫詩的關係,比作情人或靈魂伴侶,那麼我和散文寫作的關係,某天會不會變成後來的家人?
(故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