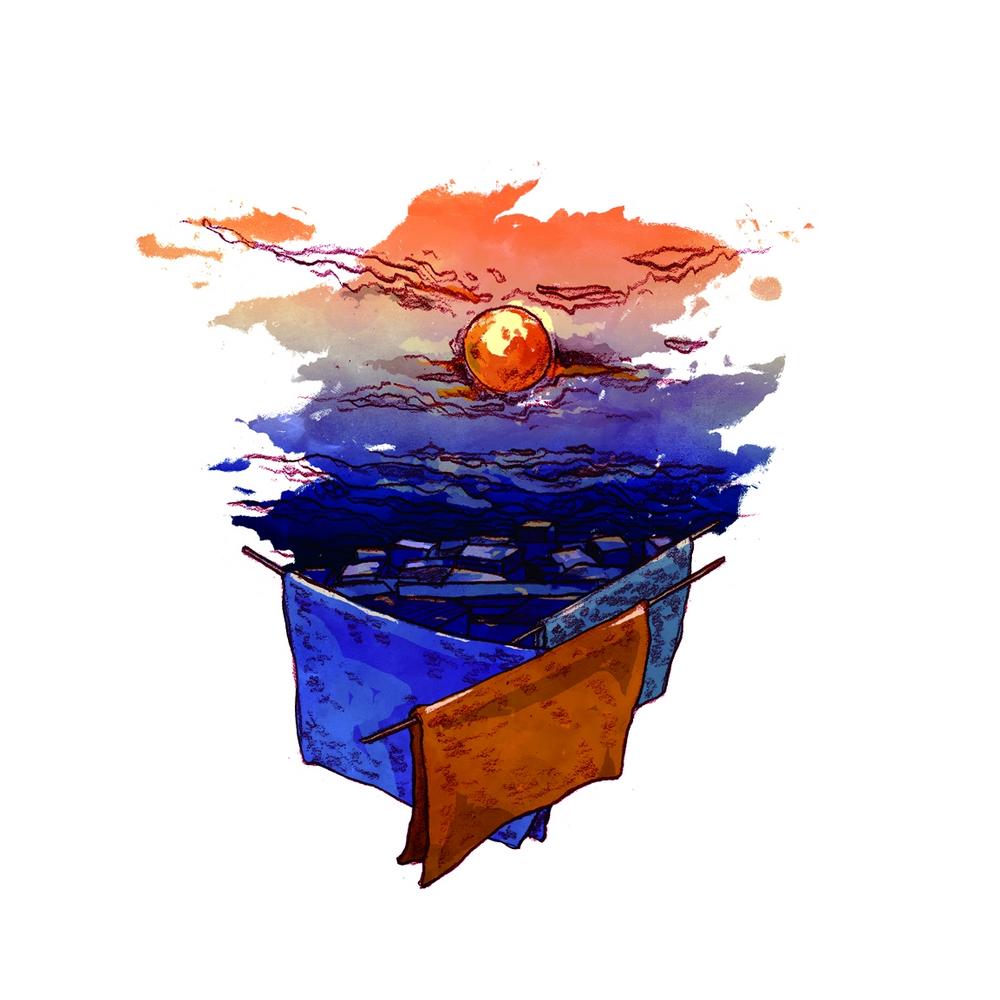羲和敲日玻璃聲
曾經,我每天清早安詳地走過墳場外蜿蜒的粉綠色圍牆,邁着有節奏的步伐上班去,絲毫沒有靠近死亡的感覺。即便祖輩都曾經躺在裡面,我們小時候入內掃墓,也從未覺得陰森可怖,只記得那裡有很多美麗的墓碑,門內還有個小教堂。小城故事未登錄於歷史舞台的年代,除了葬送時刻,平日墳場內人跡杳然,靜靜的;多少個風朝露夜陰晴天,亡魂在圍牆內享受鳥語花香,幽幽說着各人的故事。那是一本小城幾百年的歷史書。除了安葬有年或有特殊地位的亡者,墳場後頭的尋常百姓墓地,五年租用期限一到,便要“起身”另遷埋骨所;翻起了泥土的墓穴,迎來另一位新客。黃土是生命的歸宿,我們老早便意識到,這是每年掃墓都認知的事實。每次掃墓完畢,我們遊走在墳地石路間,愉快地檢視親友或社會名流的安息地,欣賞遠逝洋人墓碑上的小天使,屈指計算一些年輕殞落的生命的歲數。這是算術科減法的實習場所,小指頭一旦算出個低位數字,會嘩一聲叫起來:好年輕啊!那時我們不知道,關於壽夭,千百萬條算題雖不同,始終只能是減數。人生本就一盤減數。
死亡就是生命的消失。但主體生命的成長力量,原來可以強得壓縮由旁人消失而來的空洞。即使消失的,其實是與我們感情滿滿的親人,如祖母或外婆。人老了就要死的觀念強勢支配腦袋。至於感情不過爾爾的老人消失,如祖父,我甚至覺得是一件好事,起碼從此他便不能再追打小腳的祖母,及時止住了我對中國老輩男家長的痛恨。而無論感情深深淺淺的長輩自人間消失,一番喪葬儀式過後,很快,生活又回到日常。我們長得越高,老人在地上消失得越多。姑母四十歲時,有天我在走廊看見穿着清淡旗袍的她掀簾外出,覺得她應該快死了。那年我不到十歲。半世紀之後每次在老人院和她作別時,我卻但願她能長命百歲。在彌留的老人床前,我常想到這瘦弱的軀體所承受的苦難。社會和家族沒有為她帶來絲毫幸福,歷史的巨輪無情輾過她孤獨的一生。
我甚至好像明白了為什麼那個時代眾多的小城女性,包括年長的堂姐,都滿腔熱血投奔革命去。脫下天主教女子中學的米白旗袍校服,換上白衫藍褲梳着兩條粗黑麻花辮的堂姐在木樓梯轉身依依辭別老祖母的一刻,彼此大概都不知道,沖開祖孫的,是時代的洪流。會面安可知。那的確是個需要改革的時代。可六十年代我們再見這當年的熱血青年,她看去只革掉了自己的理想;而留下來的做小學教師的姑母,坎壈終身,也沒賺得多少美滿前途。我看見她在死亡的邊緣痛苦掙扎,知道生命的休止符即將響起。年近花甲的我,凝視死亡的力量不再,離別的傷感,不只因老人隨時的消失,還有她生命中的我們,和我們生命中的她,相牽相繫。生與死的界線,不是生者看着死者消失而已。
老人院常是等待死亡的地方,長者生命的最後一站。姑母在院舍的日子,床位有時被移到大堂,方便員工照顧吧。幾個精壯的婦人站在大堂中間的圓環工作枱前,一面摺疊衣服,一面調笑旁邊長椅坐着的幾個東歪西倒的老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塌了半邊臉的女子,五官擠在一起,側着頭憨笑。員工高聲向我介紹,她是這裡的人瑞,但已忘了自己有多大,應該一百○四歲吧,餵食時常偷偷把食物吐出,放入自己口袋中,很頑皮。我飛快心算一下,這出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百歲老人,由清末來到千禧,世界翻轉了幾回;今天她默默在這裡等待殘軀歸故土的一刻,她能感覺生命、感覺自然、感覺人間溫暖嗎?事實她已和世界相忘相失,放入口袋的食物是她踏向死亡幽谷征途上的糧餉,院舍是人間最後的驛站,員工的調笑是唯一送行的吶喊。
死亡有時是讓人嗟嘆的心靈陰影,這是生命教育的重要部分,自修的,沒有學分。雖說本城人均壽命位居世界前列,人口普遍老化,卻別以為生逢“壽”世、人人可享長命百二歲。凡事總有參差。我退休後最感難過的事情之一,莫過於偶然聽聞有學生英年早逝。年輕人如昔日的我,以為人老了才會死亡,一旦見到同窗猝逝,在消化壞消息時,他們都無法接受,感到震撼;怎麼生命好端端的便奄忽化飛塵?霎時作別同輩的陰影第一次出現時,往往也帶來可貴的生命覺醒:健康的、命運的、宗教的、思想的、感情的……。不免沉湎於哀傷與沮喪一段時日,然後又欣然前行,繼續努力建立自己的未可知。來日他們會漸漸接受無常,意識之外的死亡陰影不時衝擊,像燃點生命長城的烽煙,一縷輕煙是一聲嘆息,警醒珍惜生命的當下與美好。
沒有比看着父母離去更令人害怕死亡。自我們出生,他們的存在似理所當然,無論上學、上班、旅行或移居,凡出外,只要肯歸來的,堂前自有家長在。沒有父母的家不是家。他們奔赴黃泉的那一天,我們悲痛欲絕,沒有覺醒,不懂量度他們的歷史腳步,絕不感恩蒼天讓他們活過多少年,多少年都嫌不足。我們對死亡無比害怕,生命的來路驟被截斷,從未有過的巨大空虛侵蝕着崩塌的心靈;我們向沒入黑洞的身影瘋狂揮手,他們漸漸消失不回顧。從此杳杳長暮,千載不寤。
和七十歲或更老的自己相遇時,我聽到羲和敲日玻璃聲,開始閱讀死亡,由知道死亡到害怕死亡,檢視一路走來的諸般傷逝情懷。歲月忽已晚。死亡熱情靠近的日子,我把身上的醫療數據不時重溫,那是內科醫生用盡所有入侵性偵查手段深入敵陣般找出來的維生數字,麻醉師帶領我實習死亡,外科醫生喝令我重生:醒來!維修工作已完成。我又揭開生命歷史的舊章,長長的親疏清單顯示,血行血散,無關道德學問,也不賴辛苦經營。我見過有人自忖基因不良,恐壽夢成空,於是為非作歹,結果仍騰達安好。而即使充分掌握科學、基因、環保和營養等知識的清流,趨吉避凶,到頭來大司命還是莊嚴宣告:人命有當。昔日故居所有老人都順從地在自己的時辰躺下,我所敬重的師長輩在讀懂天地古今後,眾皆長醉不願醒。年華一旦消逝,十二玉樓無故釘。生命的意義在涯涘有盡,有盡才完整,這是人在老境必須以歡欣的笑容信賴的真相。
更深人靜,萬籟都寂,四圍一片漆黑,窗外不遠處的醫院大樓徹夜燈火通明,照亮一片社區,那是人們生命的終點,也是起點。舉頭,看得見羲和揮動長轡,拍打日輪,正沉沉奔向扶桑之檻。明天,聽得見美妙“必剥”玻璃聲的人,只消自問,我曾在哪裡建立了自己?
吳淑鈿